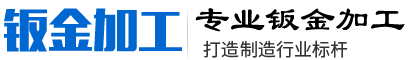HASH GAME - Online Skill Game GET 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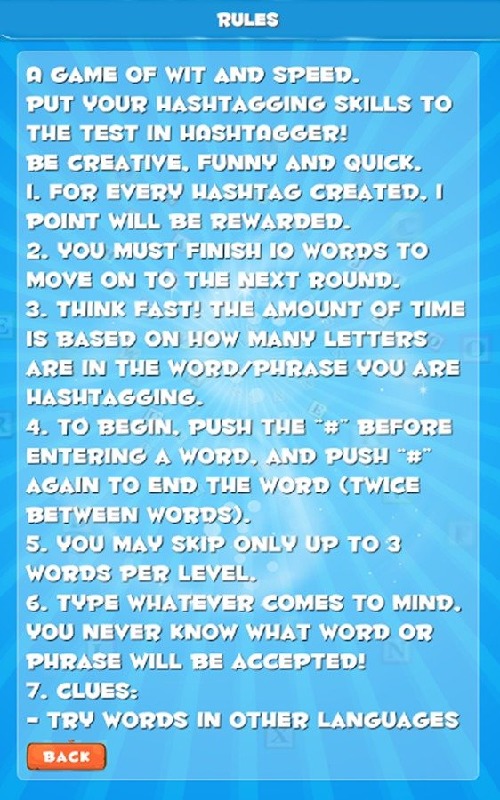
1946年6月,也就是玛莎·盖尔霍恩(1908-1998)抵达纽伦堡的几个月前,她的话剧在伦敦大获成功。这完全出乎她的预料。毕竟,这部剧本最初不过是一个冲动的念头,只是友人说服了她,让她将之付诸笔端。在此之前,这位38岁的女作家从未涉足过剧本写作,也没有这种打算。她发表过一些长篇和短篇小说,但她首先是一名坚定的新闻记者。盖尔霍恩热爱新闻事业,因为新闻总能带给她“见识和学习新事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她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通过报道揭示社会的不公。
1941年,战事正紧,同事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一番言论激怒了盖尔霍恩,因为他在伦敦的国际笔会大会上表示,作家不应当在这个时代继续写作。对此,盖尔霍恩在一封写给出版商麦克斯·珀金斯(Max Perkins)的信中愤怒地反驳道:“只要一个作家还有一丝勇气,他就应当在任何时代都坚持写作。世界越糟糕,作家就越应该努力创作,因为即便做不了什么建设性的事,来让这个世界更适合人们生活,或是减少世间的残暴和愚蠢,他至少可以记录。除他之外,没有人会做这件事,但这又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对那些遭到侮辱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指望的复仇:有人会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他们的遭遇。”盖尔霍恩不是一般意义上那种客观中立的记者,相反,她的文章从来都观点明确、立场鲜明、满怀关切。她的报道既是对人类苦难的动情描绘,也是一种愤怒的控诉。对她而言,新闻报道是教育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的一种手段。
盖尔霍恩为人们的悲惨遭遇和当权者对权力的迷恋愤愤不平,正是在这个动荡的战争年代,她找到了她的使命:战地记者。她后来写道:“若不是身处战争那普遍的混沌中,我个人的无序便无处安放。”作为战地记者,她常年随军奔赴前线。从西班牙内战到越南战争,再到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她的报道从未缺席,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盖尔霍恩是这场战争最忠实的记录者之一,此外,她还是女性战地记者的先驱,在这个几乎全由男性霸占的领域,她的存在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她的成就不仅要归功于她卓越的写作能力,还得益于她无止境的好奇心、勇气和杰出的社交能力。她非常善于倾听,即便是在炸毁的地下室或是泥泞的田地间,伴着廉价的威士忌和来自五六个不同国家的士兵用英语、德语或法语七嘴八舌地聊天,她也乐在其中。
同样是这份好奇心,让她在1936年的圣诞节和欧内斯特·海明威走到了一起。他们是在基韦斯特的一间酒吧里偶然相遇的,当时她正和母亲在那里度假。一天下午,一个“身材高大、不修边幅,穿着皱巴巴、沾着污渍的白短裤和白衬衫的男人”坐在了她对面。她鼓起勇气和这位她仰慕的作家攀谈起来。他外表邋遢,当时已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但这没能阻碍他们把谈话变成一场调情。这种关系很快便更进一步。1940年,海明威与妻子离婚,和盖尔霍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玛莎·盖尔霍恩出生于圣路易斯,有一半德国血统。她的父亲是一名德裔妇科医生,有着犹太血统的他为了躲避反犹主义的浪潮移居美国;母亲则来自上流社会,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还是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朋友。盖尔霍恩后来常常提到,父母在这段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耳濡目染也间接导致了她与海明威婚姻的破裂。她的童年很优渥,接受的是私立学校的教育,还常去欧洲旅行。长大后,盖尔霍恩顺利升入距离费城不远的布林莫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但她很快就发现那里令人窒息的氛围和中西部的家乡别无二致——终其一生,她最害怕的便是无聊。
年轻的盖尔霍恩于是中断了学业,踏上了记者之路。她在几家报社工作过,还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和海明威相遇时,这位活泼的年轻人已然成为当时文学界的新星。她的短篇小说集《我亲眼见过的艰难时世》(1936)大受好评,她在书中描绘了一系列在大萧条中挣扎求生的人物,从年轻的,到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老妇人,他们的故事都相互勾连。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书评中对这部作品赞赏有加,还称盖尔霍恩的文风“毫无女性化的色彩,令人吃惊”。媒体将她的写作风格与海明威相提并论。正是因为有这层渊源,当自信而迷人的盖尔霍恩主动与海明威攀谈时,后者也十分受用,更不用说她还将他视为文学上的大师。早在1931年,盖尔霍恩就在文章中提及,她的座右铭正是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话:“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是决不会有事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盖尔霍恩一直在德国追踪报道希特勒的崛起。1938年春天,也就是《慕尼黑条约》签署短短几个月前,她还曾去到捷克斯洛伐克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经历都被她写进了小说《被蹂躏的土地》(1940)中。战争期间,她持续为《柯里尔周刊》撰写报道,为此到过芬兰、香港、缅甸、新加坡、爪哇、加勒比海和英国。由于没有获得官方的记者证,她不被允许随军亲眼见证诺曼底登陆。于是,她躲进了一艘医疗船,并在登陆时假扮担架工混入军中,成为D-Day,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登陆诺曼底的唯一一名女记者。
1940年12月,盖尔霍恩与海明威结婚,在此之前,二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古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明威对盖尔霍恩的长期离家愈发不满。在她1943年离开哈瓦那附近的庄园、赶赴意大利前线报道时,他写信质问她:“你究竟是个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女人?”诺曼底登陆前夕,他自己也来到了欧洲前线。盖尔霍恩有自己的任务,但他总是试图阻挠她的行程。最严重的背叛发生在1944年春天,海明威也向她工作的《柯里尔周刊》自荐,想要成为战地记者,而编辑部在欧洲前线只需要一名记者,名气更大的海明威得到了这份工作。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对她的独立和他眼中的种种挑衅行为有所不满,这次背叛更是让盖尔霍恩倍感受伤。但盖尔霍恩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她之所以在诺曼底登陆时“偷渡”上那艘医疗船,就是为了写出比海明威更真实的报道。
海明威尝试过控制盖尔霍恩,遏制她的职业抱负。据盖尔霍恩所说,他甚至希望她以“玛莎·海明威”为作品署名,好让她所有的创作都和他产生关联。她的一半德国血统也成了海明威攻击的对象,盖尔霍恩选择离婚并改回她的德国姓氏时,他斥责她流着“普鲁士的血”,是个“泡菜佬”。二人离婚后,盖尔霍恩再也没有给过他一句正面的评价。她将自己描绘成单方面的受害者,但她的性格比起海明威也不遑多让。许多人认为她死板、严厉,不够通情达理,她的固执和专横连亲近的家人也难以忍受。她在1969年写给养子桑迪的信中尖刻地批评他:“动力来源于勇气、想象力和意志力,是由内而生的。而你什么都没有。”她直言道:“在我看来,你是个愚蠢的可怜虫。如果我是你,我会羞愧得从悬崖上跳下去。”盖尔霍恩报道中体现出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只留给了战争的受害者。她的养子在寄宿学校长大,染上了毒瘾,还有过犯罪经历。
在与海明威正式离婚前几个月,盖尔霍恩已和美国的詹姆斯·加文将军(General James Gavin)有了外遇,后者是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也是战后美国驻柏林占领军总司令。他的身份对盖尔霍恩很有意义,因为通过这位前线指挥官,她能够直接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二人的相遇堪比电影:在阿登战役期间,第82空降师的士兵在战场上意外发现了盖尔霍恩,她当时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穿任何制服,正独自在雪原上跋涉。士兵于是把她带到了加文所在的指挥部。盖尔霍恩和这位美军最年轻的师长迅速陷入热恋爱火从被解放的巴黎燃起,一直烧到废墟中的柏林,直到其后主演《纽伦堡的审判》的玛琳·黛德丽出于嫉妒散播了有关盖尔霍恩的谣言,自己则与加文展开了另一段恋情为止。已有家室的加文原本打算与盖尔霍恩结婚,但她完全无法接受作为军属的生活,便以加文出轨黛德丽为契机,在1946年结束了这段关系。
尽管盖尔霍恩一生中有过好几段恋情,也曾再婚复又离婚,但在旁人眼中,她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还是海明威。人们总是仅仅把她视作海明威的妻子,不断在她面前提起他,这让盖尔霍恩十分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夫妇二人都是战地记者,这样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问题——竞争心理、长期分居,以及一方对性别角色太过刻板的理解,它们都悉数体现在了盖尔霍恩的唯一一部剧本、1946年6月在伦敦大使剧院首演的《情迷新闻》中。这出戏也是她对前夫的一次隐秘的报复。
这出喜剧的两名主角,安娜贝尔和简,是两位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她们的爱情生活都很不顺心,却反倒在战争中如鱼得水。故事发生在南意大利前线的一处记者营,两位主角置身于一群男记者中。安娜贝尔正在考虑和同为战地记者的丈夫重归于好,但后者总是给她的生活制造麻烦,窃取她最精彩的“故事”,并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表,还声称:前线报道这份差事本来就太过危险,不适合女性。简则爱上了一名负责公关的军官。但当后者向她描绘即将到来的战后生活,并畅想要在一座无聊至极的庄园里定居时,一度被肾上腺素蒙蔽的她果断抽身离去。
《情迷新闻》是盖尔霍恩和同事弗吉尼亚·考尔斯(Virginia Cowles)于1945年在伦敦共同创作的,剧本的创意来自考尔斯。盖尔霍恩在戏单中写道,这部作品并不严肃,只是为了博观众一笑,顺便赚些钱。故事的背景取自盟军收复意大利期间,二人在南意塞萨奥伦卡记者营的真实经历,而两名主角的原型显然是这两位记者本人。尽管盖尔霍恩强调,剧本中的男性角色纯属虚构,无意影射任何人,但剧中安娜贝尔的丈夫乔·罗杰斯显然是在暗讽海明威。乔是一位知名作家,同时也是个酒鬼(“整天都醉醺醺的”),对妻子的成功耿耿于怀,还抄袭她的作品。用安娜贝尔的话来说,“现在看来,他娶我就是为了让这位对手闭嘴”。旁人曾提到过一则逸事,称盖尔霍恩和海明威曾偶然目击了一枚德国V2导弹从他们上空飞过。据说,盖尔霍恩当即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并警告海明威,这则“故事”是属于她的——在这位叙述者看来,此事足以证明她是多么担心他会抢先一步。
早在1944年海明威逗留伦敦期间,他也写过一则关于两位女战地记者的小品文,嘲讽她们轻浮放荡、道德败坏。可以想见,他在塑造珍妮特·罗尔夫这个优雅而野心勃勃的金发女郎时,心中所想正是盖尔霍恩这位“亲爱的、虚伪的”。实际上,尽管晚年的盖尔霍恩不愿再被问及与海明威的婚姻,但她年轻时确利用过后者的名声,来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被蹂躏的土地》的书封简介中,她骄傲地自称为“玛莎·盖尔霍恩(海明威夫人)”。《情迷新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海明威这则小品的回应。
虽然《情迷新闻》的创作时间在盖尔霍恩入住记者营之前,但这部作品中展现的女记者处境与施泰因的实际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合。二战期间共有140名女记者随美军奔赴战场,学界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关注她们的生平和成就的著作,她们面对的种种偏见也逐渐为人所知。长期以来,她们的工作都没有得到男性的认真对待。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SHAEF)规定,一场战役一旦打响,女记者就应当与护士一样驻守后方,禁止深入前线。女性被禁止独自出行,人们不愿为她们配备司机和吉普车,甚至连她们的职业道德也遭到了质疑。新闻官查尔斯·马达里,也就是后来施泰因记者营的负责人,曾在卢森堡的一次采访中向对方保证,这些女记者工作勤奋,不会给他造成“太多麻烦”。但他也透露了几则逸闻,以取笑她们的工作态度。据他所说,女记者们在巴黎期间完全无心工作,她们宁可去看时装秀。
玛莎·盖尔霍恩对这样的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并不陌生。不仅是海明威,她的主编们也一度对她怀有成见。《柯里尔周刊》给她的文章撰写的导语中常常给她贴上“小妞记者”的标签。她的部分报道配有手绘插图,但这些插图在今天看来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例如,1940年1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配图就把盖尔霍恩描绘成了一位美艳动人的女记者,金发蓬松、涂着口红,穿着凸显身材的紧身长裙,宛如新闻界的丽塔·海华丝。事实上,在现存的照片中,她的衣着始终朴素而轻便。
如果这位记者所言属实,那么被关在门外的人里也包括英国人丽贝卡·韦斯特。她和盖尔霍恩在纽伦堡的确见过面,尽管双方都没有留下相关记录。盖尔霍恩在1946年9月底抵达纽伦堡,二人都出席了判决的宣布,并且在这之前就彼此认识。对于盖尔霍恩来说,这次重逢多少有些尴尬,因为韦斯特儿子的生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935年向盖尔霍恩求过婚。甚至有流言称二人之间有过一段情史,而韦斯特对此一无所知。盖尔霍恩虽然钦佩韦斯特的写作才华,但还是与后者保持了距离。她很难与这位年长的记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尽管这并不影响她对她的尊重,她还是认为韦斯特有些神经质,而这还只是“过于温和”的说法。1987年,韦斯特去世三年后,盖尔霍恩致信她的传记作者维多利亚·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ning),向她表达了对韦斯特成就的敬仰,也直白地提到了同她沟通的困难之处:“你是怎么看待她对八卦的热衷的?……我不擅长议论别人,我觉得恶毒和仇恨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至少值得尊重。”
然而,善于仇恨也正是盖尔霍恩和韦斯特的共同点——尤其是对德国人的仇恨。“这是一个怎样的种族啊,这群德国人?既然我们试图根除疟疾,那为什么不花些时间,把德国人也彻底消灭呢?他们造成的死亡更多,手段也更恶劣。”这是盖尔霍恩在1944年8月写给朋友霍滕丝·弗莱克斯纳(Hortense Flexner)信中的一段,那时她刚在意大利目睹了她从未见过的最残酷的景象。那是一个万人坑,里面埋着320名被德国人枪决的人质。写信时的她还不知道,更为可怖的场景还在后面。
1945年4月29日,盟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几天后,盖尔霍恩便抵达了现场,展开报道。那一天是5月7日,德国投降日。盖尔霍恩在战争中从未受过伤,甚至连擦伤都没有,但达豪的见闻刺伤了她。她后来回忆,那时的感受如同跌下了悬崖。作为战地记者,盖尔霍恩的足迹遍布半个地球,常常见到满地尸体像包裹一样躺在街上。“但没有一处能与这里相提并论。那些饥饿的、受虐的、赤裸而无名的尸体横陈着,没有一场战争中出现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景象。”她写道,幸存者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失去了任何个人特征,也分辨不出年龄。在那些枯瘦的面孔上,已经很难找出足以区分他们的相貌特点。一些囚犯曾被用作人体实验:纳粹把他们暴露在低氧环境下,以测试飞行员在高空中的生存极限;把他们浸入冰水中,研究极端的低温对人体的影响;给他们注射疟疾病原体,寻找为德国士兵研发对应疫苗的可能;另一些人则被强行或绝育。
盖尔霍恩在写给《柯里尔周刊》的报道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暴行,还采访了一位集中营的波兰医生,他本人也曾是囚犯。人类竟能做出这种魔鬼般的行径,这让他感到既愤怒又羞耻。谈话中途,盖尔霍恩一度因无法继续而中断了采访,只能转而查看集中营的其他地方,然而在铺天盖地的恐怖之中,她几乎找不到任何喘息之机:和电话亭一样狭小的审讯室、堆满尸体的毒气室——党卫队还没有来得及焚烧它们。在踏进毒气室时,甚至有人劝她用手帕遮住鼻子。她还在达豪见到了一名布痕瓦尔德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他的身体或许会活下去、再度恢复力气,但很难想象他的眼睛还能找回普通人那样的神采。”一些囚犯在获救的狂喜下猝死,还有人因为饥饿过久而暴饮暴食,他们的身体却已无法承受。一些人欣喜地奔向他们的解放者,却在途中被电网夺去了生命。盖尔霍恩正是在达豪听到了欧洲胜利的消息,她也因此将这里视作战争的象征。达豪就是战争的缩影,而胜利只有在所有的达豪都彻底消失时才会到来。
至少有39名德国卫兵被美军当场射杀,他们当时已经投降。玛莎·盖尔霍恩对此由衷称快。“在成堆这样的死尸后面,躺着那些衣冠楚楚、身体健康的德国士兵的尸体。他们驻扎在集中营,在美军突入时被当场射杀。见到死人第一次成了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她没有提到的是,这些死者属于一支不久前才被征召的预备役,其中一些士兵还是少年,而负责管理集中营的党卫队骷髅总队早已逃之夭夭。或许盖尔霍恩对此并不知情,即便如此,报复的念头对她来说也并不陌生,甚至成为贯穿在她作品中的母题。
基于达豪的见闻,盖尔霍恩在小说《覆水难收》中描绘了一段彻底的复仇幻想。小说出版于1948年,它带领读者跟随欧洲战场上一个美军步兵营经历了“二战”最后的几个月,从阿登战役到死亡集中营的发现。主人公雅各布·莱维是一名来自圣路易斯的年轻士兵,在此之前,他从未关心过政治、世界局势或自己的犹太出身。但在亲眼见证达豪集中营的解放后——他在集中营内走过的路线几乎和盖尔霍恩的亲身经历一模一样——他被迫直面超乎他想象的非人行径。幸存者海因里希已经在集中营中被关押了十二年,他向莱维平淡地讲述了酷刑和大屠杀的种种细节,这已经成为他的日常,而在莱维眼中,这种命运本可能降临在他自己头上。在此之前,他也对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所耳闻,但从未真正意识到它恐怖的规模。他迄今为止的人生都建立在一种幻想之上,认为自己只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就能生存下来,甚至取得成功。然而这些犹太人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他们想要的也不过是正常的人生。
达豪的冲击彻底改变了莱维。回到吉普车上,他看到一群说说笑笑的德国女人站在路中央,听到他的喇叭声却无动于衷。仇恨席卷了他,他失控地发动汽车,猛踩油门,冲向那群女人,把她们碾在车轮之下,自己则撞上了一棵树。在医院里,莱维承认自己犯下了谋杀罪,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意味着他终于接受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相应地,他也感到有义务牺牲个人的幸福,来让世人直面他们在大屠杀发生时袖手旁观的罪责。莱维最终被判过失杀人,免予监禁,故事也在此落下帷幕。
盖尔霍恩在后记中写道,她创作这部小说是为了驱逐那些挥之不去的画面,她已经无法再背负着它们生活。和莱维一样,她也没能在战争期间关注到集中营的惨状,没能为之发声,她也曾拒绝直面事实,因为她根本想象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无论盖尔霍恩如何想方设法为书中这起虚构的谋杀辩解,它依然是一种无差别的报复。同样,她固然有理由感到愤怒,有时却难免片面和偏颇。与盖尔霍恩的大部分作品不同,《覆水难收》从未被翻译成德文。
1946年9月底,盖尔霍恩抵达了这座位于弗兰肯的城市,此时达豪之行已经过去一年有余。9月30日,她第一次进入法庭旁听,那是整场审判的倒数第二次庭审。她在笔记中写道:“戈林有着我见过最丑的拇指——说不定也有最丑的嘴巴。”在她看来,他的微笑与整张脸完全不协调,更像是一种习惯动作。法庭内的空调开到了最大,室内很冷,仿佛是在呼应法官的语气。没有任何同情的余地,盖尔霍恩写道,面对全无人性的纳粹分子,人们只能回以冷酷。
审判闭庭后,盖尔霍恩很快为《柯里尔周刊》写出了一份正式报道。在文章开头,她先是勾勒了被告们的神态:戈林勉强挤出的微笑,里宾特洛甫僵硬的姿态,凯特尔石像一般的面孔。邪恶在这里获得了具体的面貌,但“它们都不过是脸。一些人的长相更加粗鲁,但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平平无奇。毕竟,这些人终究只是人类,长着两条腿、两只手臂和两只眼睛,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既不是十英尺高的巨人,也没有戴着麻风病人的丑陋面具。坐在那里、注视着他们,会让你的心中油然生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愤慨。这21个人,这些微不足道的存在,这些不知疲倦的、曾经不可一世的怪物,就是那个经统治着德国的小帮派仅剩的成员”。盖尔霍恩希望她的读者看到这些男人作为个体的渺小,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纳粹主义的恐怖化身。
9月30日晚,盖尔霍恩与记者营的其他记者前往安斯巴赫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在那里,他们和一个年轻的德军士兵交谈了起来。那是个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德国之所以加入战争,是因为英国人早已准备发动袭击。“那么德国最先进攻的为什么是波兰,而不是任何一座英国城市?”他无言以对,却还是坚信他的政府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他说,集中营的死亡人数一定是被夸大了,把犹太人送到那里,是为他们自己的安全考虑。杀害犹太人是错误的,但这些人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工作,据他观察,他们自有一套狡诈的敛财手段。在他心中,希特勒青年团仍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当发现这些话完全没有打动听众时,他显得十分困惑。
盖尔霍恩在施泰因的记者营只待了几天。或许是觉得这里的生活乏善可陈,她留下的文字中从未提过这段日子。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她已经习惯了比这更恶劣的居住条件。西班牙内战期间,她与海明威和其他记者同行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那里是炮火的固定目标,部分房间已经被炸毁,电梯常常失灵,连热水都是一种奢侈品。她在前线住过临时营房,经常只有罐头食品充饥。和从未做过战地记者的威廉·夏伊勒不同,对她而言,法贝尔堡的生活条件已经称得上舒适,哪里值得大惊小怪?盖尔霍恩的写作总是为了表达她的关切,她宁可把笔墨用于记录达豪的恐怖和这场世纪审判。对她来说,纽伦堡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审判刚结束不久,她已经准备动身前往巴黎,去参加即将闭幕的巴黎和会。
德国之行给盖尔霍恩留下的是对一切德国事物的反感,这样的反感伴随了她一生。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她都尽可能远离德国,直到1962年,在耶路撒冷参加艾希曼审判的半年之后,她在《大西洋月刊》的委托下再次踏上了一场“短暂的地狱之行”,以考察新一代德国人的面貌。她在德国逗留了三周,造访了从汉堡到慕尼黑的多所大学,与那里的学生们交谈。然而,就像此前的丽贝卡·韦斯特一样,盖尔霍恩事实上也坚信德国人“无药可救”。早在1943年,她就在给海明威的信中提到过,她读完了范西塔特勋爵的著作,并十分赞同他对德国的看法。她向一位熟人提到,现在的德国人或许看上去像是“休憩的绵羊和老虎”,但这只是因为他们被黄油和奶油喂得体态臃肿,又得到了消费主义的安抚。“一旦把这些统统拿走,他们又会变成疯狂嗜血的绵羊和吃人的老虎。”那些女学生尤其令她震惊。她们保守、无趣、毫无幽默感,对权威俯首帖耳,堪比“西方的阿拉伯妇女”。在《新德国是存在的吗?》一文的结尾,她以坚定的否定回应了标题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新德国’,有的只是‘另一个德国’。德国需要一场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革命,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到来。那不是一场血腥的传统革命——先是行刑队,再是监狱,最后以建立另一个独裁政权告终——而是一场内在的、头脑和良知的革命。”
在那之后又过了二十八年,盖尔霍恩才再度踏上德国的土地。1990年,德国统一之际,她重新走访了当年的几座大学。她想知道,在此期间是否又诞生了新一代的德国人。她在《我除外:我为何决定不再重返德国》一文中写道,起初,这种希望的确得到了印证。她观察到了某种心态上的变化,这意味着“六八运动”确实对德国产生了影响。“他们接受的教育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如今能够独立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接踵而至的就是霍耶斯韦达的种族主义暴动、罗斯托克新纳粹团体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以及蔓延整个东德的新纳粹主义。在盖尔霍恩看来,德国政府对这一系列颠覆活动的遏制远远不够,而在政府的不作为之外,更令她不解的是,新一代的学生们去了哪里?“那些好孩子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学里没有人对无能的政府和新纳粹分子的举动发出抗议?她失望极了。在这种挫败下,她甚至将德国人的无所作为归结于基因问题,并倒向了一种看似从生物学出发,但归根结底仍带有歧视意味的解释:“我想他们一定是某个基因出了问题,尽管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既然如此,她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再重返德国了。盖尔霍恩信守了诺言。1998年,她在伦敦离开了人世。